【原创文学】同居长干里
作者:余悸
2002年12月28日夜
版权所有,谢绝转载
北京来的房客搬过来时,爸爸妈妈在镇外的小树林里找到我,我得意地跟他们炫耀刚刚捕到的一堆知了,他们却拖我回家。于是我在客厅看到一个优雅的妇人和她背后因为羞涩和惊惶而躲躲闪闪的小女孩。我大咧咧地微点点头,说:“你们好。”妈妈在一边提示:“该叫阿姨。”我惊讶地回过头问妈妈:“她们俩我都叫阿姨?”妇人乐了,轻摸着我的头对我爸爸妈妈说,这孩子很调皮啊。小女孩也开心地笑了起来,而且居然还走了过来,对我伸出手:“我叫苏蔚,今年10岁。”我却莫名其妙地不好意思起来,先是也伸出手,却没敢跟她的手握,而转道去摸鼻子,然后讪讪地笑,“你的普通话真好听......我叫陈皓,也是10岁。”
后来我就正式管苏蔚她妈妈叫阿姨。从大人的一些断续交谈里得知阿姨其实是本地人,而且是爸爸的老同学,年轻时在北京求学并嫁在那儿,多年后有了一些变故,便带着苏蔚回家乡。一时找不到合适房子,就暂住我们家楼上。在我眼里阿姨是个很神秘的人,穿着做工精致本地市场上根本没有的衣服,深居简出,每天就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用普通话有些矜持地跟我妈闲聊家常。
开学后苏蔚办好了转学手续,进了我读的学校,却只是读三年级,比我低一个年级。那天下午苏蔚气鼓鼓地找到我们四年级教室,让我陪她去找我那做校长的爸爸。我正在指挥全班排练开学大会上的合唱,小小的虚荣心极度膨胀之下,就很潇洒地说,“你看,我好忙啊,你去教室外面等我吧。”直到夕阳最后一抹余光也消失的时候,我还兴致高昂着,同学们却纷纷抗议起来,我只好宣布解散。意犹未尽地出了教室门,看到苏蔚娇弱的身影斜靠在偌大的墙壁上,我怔了半晌,然后低头走到她面前说对不起。她不说话,只看着我,眼里有泪光。
晚上我跟爸爸吵得不可开交。他反复解释说是怕苏蔚不适应乡镇小学的教学环境,特意给她安排了低一年级。我不依,一口咬定他不考虑苏蔚的感受。爸爸终于烦了,“你一个小屁孩儿,怎么管得这么宽。”我不买账,把饭碗往前一推,跟妈妈说我不吃了,回房间做作业。妈妈要拉我,爸爸不许,说这小子今天是纯粹无理取闹,就饿他一回,看他能闹多久。我做完作业后肚子饿得咕咕叫,但硬撑着不肯去厨房找吃的,只一遍一遍在台灯下画爸爸的变形头像来泄愤。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觉旁边有个小脸笑嘻嘻地挨着我的脸,是苏蔚。她把很多糖果放到我桌上,“知道你饿了,而且是为我饿的。给,这是我从北京带的糖果。”然后她一边说着“谢谢你”一边飞速地亲了我的额头,像只蝴蝶一样地飘走了。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睁着眼睛呆看天花板,使劲想北京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糖果和这么漂亮的女孩。而且被北京的女孩亲一下,怎么感觉比北京的糖果还甜。
苏蔚顺利地也进了四年级。第一个学期结束后,爸爸在我家和苏蔚家一起吃的晚饭上宣布:为了奖赏我和苏蔚的期末考试成绩,要带我们俩旅游,去哪里任选。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去北京。爸爸妈妈有些惊愕,阿姨的脸却阴沉下来。苏蔚躲闪着看看她妈妈又看看我,抿了抿嘴,没说话。我过去拉着她的手说就算陪我去,好不好。阿姨终于说话了,问我为什么想去北京。我说因为北京有很多东西。她冷笑,“有什么东西?有臭东西!有负心人!”然后她哭起来。
我终于没去成北京。那个寒假爸爸妈妈整天陪着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的阿姨,让我陪着苏蔚。我们一起去书摊借小人书,一起看我收集的乱七八糟的邮票,一起翻我粗陋的书画册,一起去小河上凿破冰然后钓鱼。有一天坐在小山头上,她指着远处低矮的村庄,纷乱的公路,还有成簇的树林,沉静地说,“陈皓,我忽然好喜欢这个地方。也许,妈妈和我,都是天生属于这里的。”我径自站起来,吼:“可我想去北京~~~”
开学,假期,再开学,再假期,日子流水般过去。初三时阿姨已经不能走动完全卧床了。苏蔚跟我爸爸商量要退学来照顾她妈妈,被拒绝;她不甘心,反复解释说实在不放心妈妈的身体,爸爸则表现得没有商量余地,告诉她除了读书以外的任何事都别管。我从门外探出头,冷冷地说,“苏蔚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她就跟我一起出了门。我靠在篱笆上,一言不发,忿忿地看着她。她却一下子扑进我怀里,抽泣起来。我顿时惊慌失措,双手不知怎么放才好,终于还是犹豫着把她抱紧,并如梦初醒地发现这个已经共同生活了五年的女孩早已长大,而且青春逼人。那个晚上我们就那样一起抱着,我看着盈盈月光柔和地倾泻在她的乌黑长发和洁白长裙上,如痴如醉。在迷糊中我说忽然很想谱一个曲子。她嗯了一声后说,“这首曲子就叫《长干行》吧,妾发初覆额。郎骑竹马来。”
中考后她不顾我和爸爸妈妈的反对,坚持在志愿上填了中专,好早点毕业后照顾她妈妈。而我进了全市最好的中学,和她的学校一墙之隔。每天中午和晚上她过来和我一起去餐厅吃饭,每餐饭她都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肉,说学习忙要多补充营养,然后又忙不迭地再给我加蔬菜,说还要注意营养平衡。每个周末我骑车带她一起回家,那时候总是黄昏,乡村公路上静悄悄的,只有几片树叶在金黄的日暮里盘旋着降落,她抱着我的腰坐在后座,唱歌给我听,或者听我讲笑话。有时候我还故意说一些色情笑话,引得她嗔怒地扬着小拳头使劲捶我。
高三时有个女孩开始追我。她很漂亮,成绩又并不比我差多少,于是因此很狂妄。某天放学后她把我堵在教室里,嚷:“你跟一个中专女孩在一起有什么出息?那样的女孩也值得你当宝?我哪一点不比她好一百倍?”我耐心地听她吼完,然后平静地问她,“你懂一首叫《长干行》的曲子么?”她愣了愣说,“那不是李白的诗么,怎么成了曲子。”在她愣的那会儿,我夺步走出教室,却看到苏蔚就在门口,泪流满面。我一把抱过她,温柔而又有力地亲她的脸颊,眼睛,鼻子,和嘴唇。我说小蔚你知道么,我爱你8年了,足足8年,从10岁那年你亲我开始。
我高考前夕时苏蔚毕业,而阿姨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个夏天最热的时候我收到了北京那所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之前苏蔚已在留下一张字条后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字条是我踏上北上的列车时爸爸交给我的,上面只有一句“皓,我也爱你足足8年了”。那一刻我眼角却似在站台上看到那熟悉的身影。一怔,定神再细看,却只有川流不息的人群。
爸爸拍着我的肩,说,“只能如此了。有些人注定要去远方,有的故事注定没有结局。”
2002年12月28日夜
版权所有,谢绝转载
北京来的房客搬过来时,爸爸妈妈在镇外的小树林里找到我,我得意地跟他们炫耀刚刚捕到的一堆知了,他们却拖我回家。于是我在客厅看到一个优雅的妇人和她背后因为羞涩和惊惶而躲躲闪闪的小女孩。我大咧咧地微点点头,说:“你们好。”妈妈在一边提示:“该叫阿姨。”我惊讶地回过头问妈妈:“她们俩我都叫阿姨?”妇人乐了,轻摸着我的头对我爸爸妈妈说,这孩子很调皮啊。小女孩也开心地笑了起来,而且居然还走了过来,对我伸出手:“我叫苏蔚,今年10岁。”我却莫名其妙地不好意思起来,先是也伸出手,却没敢跟她的手握,而转道去摸鼻子,然后讪讪地笑,“你的普通话真好听......我叫陈皓,也是10岁。”
后来我就正式管苏蔚她妈妈叫阿姨。从大人的一些断续交谈里得知阿姨其实是本地人,而且是爸爸的老同学,年轻时在北京求学并嫁在那儿,多年后有了一些变故,便带着苏蔚回家乡。一时找不到合适房子,就暂住我们家楼上。在我眼里阿姨是个很神秘的人,穿着做工精致本地市场上根本没有的衣服,深居简出,每天就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用普通话有些矜持地跟我妈闲聊家常。
开学后苏蔚办好了转学手续,进了我读的学校,却只是读三年级,比我低一个年级。那天下午苏蔚气鼓鼓地找到我们四年级教室,让我陪她去找我那做校长的爸爸。我正在指挥全班排练开学大会上的合唱,小小的虚荣心极度膨胀之下,就很潇洒地说,“你看,我好忙啊,你去教室外面等我吧。”直到夕阳最后一抹余光也消失的时候,我还兴致高昂着,同学们却纷纷抗议起来,我只好宣布解散。意犹未尽地出了教室门,看到苏蔚娇弱的身影斜靠在偌大的墙壁上,我怔了半晌,然后低头走到她面前说对不起。她不说话,只看着我,眼里有泪光。
晚上我跟爸爸吵得不可开交。他反复解释说是怕苏蔚不适应乡镇小学的教学环境,特意给她安排了低一年级。我不依,一口咬定他不考虑苏蔚的感受。爸爸终于烦了,“你一个小屁孩儿,怎么管得这么宽。”我不买账,把饭碗往前一推,跟妈妈说我不吃了,回房间做作业。妈妈要拉我,爸爸不许,说这小子今天是纯粹无理取闹,就饿他一回,看他能闹多久。我做完作业后肚子饿得咕咕叫,但硬撑着不肯去厨房找吃的,只一遍一遍在台灯下画爸爸的变形头像来泄愤。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觉旁边有个小脸笑嘻嘻地挨着我的脸,是苏蔚。她把很多糖果放到我桌上,“知道你饿了,而且是为我饿的。给,这是我从北京带的糖果。”然后她一边说着“谢谢你”一边飞速地亲了我的额头,像只蝴蝶一样地飘走了。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睁着眼睛呆看天花板,使劲想北京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糖果和这么漂亮的女孩。而且被北京的女孩亲一下,怎么感觉比北京的糖果还甜。
苏蔚顺利地也进了四年级。第一个学期结束后,爸爸在我家和苏蔚家一起吃的晚饭上宣布:为了奖赏我和苏蔚的期末考试成绩,要带我们俩旅游,去哪里任选。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去北京。爸爸妈妈有些惊愕,阿姨的脸却阴沉下来。苏蔚躲闪着看看她妈妈又看看我,抿了抿嘴,没说话。我过去拉着她的手说就算陪我去,好不好。阿姨终于说话了,问我为什么想去北京。我说因为北京有很多东西。她冷笑,“有什么东西?有臭东西!有负心人!”然后她哭起来。
我终于没去成北京。那个寒假爸爸妈妈整天陪着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的阿姨,让我陪着苏蔚。我们一起去书摊借小人书,一起看我收集的乱七八糟的邮票,一起翻我粗陋的书画册,一起去小河上凿破冰然后钓鱼。有一天坐在小山头上,她指着远处低矮的村庄,纷乱的公路,还有成簇的树林,沉静地说,“陈皓,我忽然好喜欢这个地方。也许,妈妈和我,都是天生属于这里的。”我径自站起来,吼:“可我想去北京~~~”
开学,假期,再开学,再假期,日子流水般过去。初三时阿姨已经不能走动完全卧床了。苏蔚跟我爸爸商量要退学来照顾她妈妈,被拒绝;她不甘心,反复解释说实在不放心妈妈的身体,爸爸则表现得没有商量余地,告诉她除了读书以外的任何事都别管。我从门外探出头,冷冷地说,“苏蔚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她就跟我一起出了门。我靠在篱笆上,一言不发,忿忿地看着她。她却一下子扑进我怀里,抽泣起来。我顿时惊慌失措,双手不知怎么放才好,终于还是犹豫着把她抱紧,并如梦初醒地发现这个已经共同生活了五年的女孩早已长大,而且青春逼人。那个晚上我们就那样一起抱着,我看着盈盈月光柔和地倾泻在她的乌黑长发和洁白长裙上,如痴如醉。在迷糊中我说忽然很想谱一个曲子。她嗯了一声后说,“这首曲子就叫《长干行》吧,妾发初覆额。郎骑竹马来。”
中考后她不顾我和爸爸妈妈的反对,坚持在志愿上填了中专,好早点毕业后照顾她妈妈。而我进了全市最好的中学,和她的学校一墙之隔。每天中午和晚上她过来和我一起去餐厅吃饭,每餐饭她都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肉,说学习忙要多补充营养,然后又忙不迭地再给我加蔬菜,说还要注意营养平衡。每个周末我骑车带她一起回家,那时候总是黄昏,乡村公路上静悄悄的,只有几片树叶在金黄的日暮里盘旋着降落,她抱着我的腰坐在后座,唱歌给我听,或者听我讲笑话。有时候我还故意说一些色情笑话,引得她嗔怒地扬着小拳头使劲捶我。
高三时有个女孩开始追我。她很漂亮,成绩又并不比我差多少,于是因此很狂妄。某天放学后她把我堵在教室里,嚷:“你跟一个中专女孩在一起有什么出息?那样的女孩也值得你当宝?我哪一点不比她好一百倍?”我耐心地听她吼完,然后平静地问她,“你懂一首叫《长干行》的曲子么?”她愣了愣说,“那不是李白的诗么,怎么成了曲子。”在她愣的那会儿,我夺步走出教室,却看到苏蔚就在门口,泪流满面。我一把抱过她,温柔而又有力地亲她的脸颊,眼睛,鼻子,和嘴唇。我说小蔚你知道么,我爱你8年了,足足8年,从10岁那年你亲我开始。
我高考前夕时苏蔚毕业,而阿姨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个夏天最热的时候我收到了北京那所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之前苏蔚已在留下一张字条后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字条是我踏上北上的列车时爸爸交给我的,上面只有一句“皓,我也爱你足足8年了”。那一刻我眼角却似在站台上看到那熟悉的身影。一怔,定神再细看,却只有川流不息的人群。
爸爸拍着我的肩,说,“只能如此了。有些人注定要去远方,有的故事注定没有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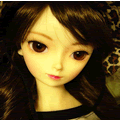

 Huasing Association 1999 - 2013
Huasing Association 1999 - 2013